
从空中望去,四川盆地犹如中国腹地一个巨型漏斗。岷江、涪江、沱江及嘉陵江则是这个巨型漏斗的整容师——它们用数百万年之久的川流不息塑造了四川盆地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这里的历史与文明都与它们密切相关。
如果说是水孕育了“天府之国”的历史与文明,那么耸立在四川盆地西部的连绵群山则更像是铜墙铁壁——它们那高大的身躯使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在受阻后变得温文尔雅,然后再进入四川盆地,为蜀地文明的儒雅描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山与水的互存,更是自然与文明的交融。
在四川盆地西部的群山之中,有一座山顶常年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直入苍穹,其以7 556米的高度傲视群山,它就是被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山。在贡嘎山的东侧,大渡河奔腾着一路向南,用时间的传送带将贡嘎山下的松散土体一点点地搬运到遥远的地方,然后沉积下来。这是地球表面物质能量的典型转换模式,世间万物都得遵循。这样的过程在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从高原隆升到河流侵蚀,每一个过程都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却是在无数个惊天动地中才得以实现。
全球为数不多的冰水阶地
虽然大渡河一直在雕琢着川西地区的崇山峻岭,但还是在贡嘎山东坡的河谷中留下了一块平坦之地——磨西台地。这是一个从贡嘎山脚下由北向南倾斜且呈长条状延伸的台地,长约11千米、高约100米,是贡嘎山早期冰川融水携带的冰碛物碎屑在山脚下低洼之处沉积而成。由于受到两侧雅家埂河和燕子沟的强烈侵蚀,经过长达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下切后形成相对于河床较高的台地。磨西台地并不是一个规整的长条形,而是总体上北宽南窄,局部还因为河流的侵蚀和台地垮塌程度不同而变得宽窄不一(最窄的地方仅有数十米,而最宽处则可达数千米)。如此大规模的冰水阶地,在全球也是为数不多的。
雅家埂河与燕子沟是贡嘎山东坡最大的两条河流。它们也是磨西河最大的两条支流,流域面积均超过100平方千米。雅家埂河位于磨西台地东侧,燕子沟位于磨西台地西侧。两条河流在空间上呈平行状由北向南而下,沿磨西台地两侧深切,也就形成了中间的这片台地。
你若是站在高处,仅凭肉眼就能从磨西台地被河流侵蚀出来的剖面上看出它的分层结构。每一层沉积物的粒径大小、颜色及厚度均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磨西台地沉积物中获取的朽木进行碳-14测年发现,磨西台地的形成前后共经历过了5次明显的大规模冰川后退。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的形成用了多长时间,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其平均年龄距今大约7 000多年。
在当地人眼里,磨西台地是一条伏于贡嘎山下的神龙——龙的头就是贡嘎山,磨西台地则是龙身——庇佑着贡嘎山下的生灵万物。当磨西台地延绵十余千米,在雅家埂河与燕子沟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戛然而止,也就意味着磨西台地这条“龙”的尾巴到此而止。
茶马古道上的变迁
龙虽然只是一种臆想的存在,但贡嘎山下的冰川地貌与高原美景则是普罗大众心之神往的旅游胜地。磨西台地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古羌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亦是汉代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历史上是川藏要道上的一座繁华重镇。一个世纪前的法国传教士沿茶马古道而来,磨西镇上中西文化融合的钟声已在贡嘎山下回响了一百多年,那座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磨西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决定了长征北上的路线,从而有了后来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磨西台地也从此与中国的现代史在无声无形中便融为了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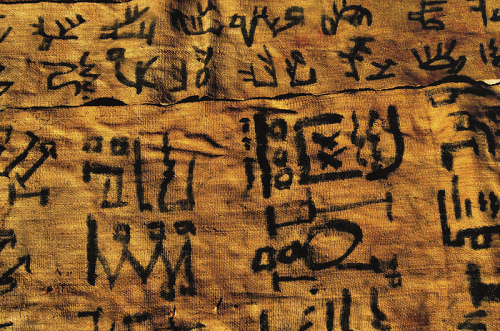
如今的磨西镇已经是国家AAAAA级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景区的核心功能区,每年承担着100余万游客们的吃、住、游等,是一个具有综合性服务功能的旅游集散地。大量涌入的游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旅游业拉动的配套设施建设强度也在日益加大。磨西台地上的房屋建筑数量在过去10年间剧增,其在大量钢筋混凝土的重压之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荷载。旅游业正在以新的速度推动着贡嘎山下的现代化进程。
磨西台地的成因之论
如果说磨西台地是贡嘎山冰川的产物,这或许没有人会怀疑,但地质学家们却对于磨西台地的成因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争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地质学家Arnold Heim到贡嘎山地区考察后,认为磨西台地是贡嘎山东坡燕子沟冰川融化后的水流搬运冰碛物在此沉积而成,其证据是磨西台地的砾石层具有明显的水动力改造痕迹。Heim的这一结论当时也得到了我国地质学家李承三先生的认同。
到了20世纪末期,对磨西台地成因的解释开始出现 “二元”成因的观点。其中,以我国冰川学家,北京大学的崔之久先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磨西台地的下部应该是冰碛物,而上部则为冰水沉积物,是由两种不同的沉积过程形成的。原因是磨西台地上部的堆积层指示了流水的搬运痕迹,而台地下部堆积层中没有明显的层理结构,应该是形成时代较久的冰碛物。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科学院郑本兴先生提出了磨西台地的“多元”成因观点。他认为在台地面上有出露地表的巨大砾石,应为冰川消融后留下的冰碛物,或者是由冰川泥石流搬运而来,并在磨西台地尾部发现了现代泥石流沉积物的证据,指出磨西台地应是由早期的冰碛物、后期的冰水沉积物及泥石流沉积物等共同作用而成,但其主体为倒数第二次冰期的冰川堆积物。此外,崔之久先生也在磨西台地西侧发现了泥石流沉积物,为磨西台地的多元成因观点提供了又一支点。
冰川融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现代文明的进程似乎从来都是伴随着各种风险同时出现的。因为人口的聚集,各种基础设施及房屋的修建使得磨西台地正“被承受”着各种现代文明的附加风险。
中国科学院的观测结果表明,贡嘎山的冰川如今正以每年约20米的速度后退。大量的冰川融水对下游河道产生更强的侵蚀,对磨西台地的安全造成隐患。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磨西台地因河流侵蚀而产生坍塌的地段多达30余处,也就是说,磨西台地正在悄无声息地变窄。


除常规的河流侵蚀外,贡嘎山地区的泥石流也频繁发生。调查表明,与平常的沟道径流或洪水产生的侵蚀相比,因为泥石流流体中含有大量的泥沙和块石,其侵蚀能力远大于洪水许多倍(一次泥石流对河道的侵蚀强度往往需要沟道径流经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完成)。从这个角度看,泥石流成为了磨西台地能否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
持续融化的冰川与磨西台地的未来
研究表明,贡嘎山的隆升与鲜水河、龙门山及安宁河断裂带形成的“Y”字形活动断裂带直接相关。GPS监测数据显示,直至今天,贡嘎山仍以相对于四川盆地约每年5~7毫米的速度向上隆升。高寒的环境为冰川的发育提供更好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叠加作用下的极端高温、暴雨等因素必将加剧贡嘎山地区的泥石流活动频率,对磨西台地的侵蚀风险也将持续增高。贡嘎山在持续隆升,冰川也将持续融化。这个过程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这座因冰川而成、又因冰川而危的冰水阶地,在地质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了贡嘎山气候的冷暖与人世间的繁华。虽然磨西台地的出现在漫长地质年代中仅是沧海一粟,但它的演化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其不可能在冰川融水的持续侵蚀下屹立不倒。我们不知道它能坚持多久,或许是数千年,或许是数万年,甚至更久。
这座曾经目睹了贡嘎山沧海桑田的磨西台地,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将是今后重点关注的话题。从长远的角度看,合理防护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问题,然后才是工程手段。这是一个需要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双管齐下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本文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川西山区城镇灾害地质调查(编号:DD20190640)”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循环冻融作用下冰碛土的碎化效应及其对泥石流启动的影响试验研究(编号:41772324)”项目联合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