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这三个地方,无论就政治而言,还是就文化而言,都已被紧紧地焊接在了一起,以至于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只要你看到其中一个字,另外两个字就那么迅速而自然地飞来与之相依,与之共存。
我总觉得他们像三个沦落于严酷环境里的弟兄,脚踏一域蛮荒,眼巡茫茫长空;不好高骛远,不俯首称臣 ;形貌粗陋,内里高洁 ;铮铮铁骨,不屈不从 ;牵心扯肺,一脉相承。
我也总是有着这样一种体验,单独地拿出西吉、海原或者固原,总觉得有一种虚茫感和无助感,总觉得有着某种意义上的欠缺与不成立,但是在大野朔风的境地里将它们排列在一起,密切在一起,立即便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亲情浓烈起来,一种完整的意义脱颖而出,一种自信和力量也就会得到不断的证实、喷涌与加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海固大都是一份沉甸甸的重量。西海固是一个超出这三个字的更大的概念。
西海固!
再三地咂吧这种滋味,再三地觉知那份含量,再三地禁不住泪漫双眼。
我们从骨子里来说已成了彻彻底底的西海固人,我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有着深刻的难以抹杀难以粉饰的西海固特征。
我们一代又一代浸泡在苦难之中。
就物质生活而言,我们确乎是挣扎于人类的最底层了。
我们到任何一个城市里去,都让人家一眼看出我们身上严重的封闭与土著,由于我们落生在西海固,由于我们身上深刻的西海固烙印,似乎一切城市都与我们没有关系了。
说真的,我到任何一个城市里去,都有一种强烈的陷身牢狱的感觉,我时时处处感到城市对我的排斥与敌意,我感到那些大楼对我的俯瞰与嘲弄,我感到那些繁华的陈设故意在我面前显露出冰凉的贵族气息。甚至一片树叶,因为它生在城市,又归宿于城市,因而在它那小小的脸上也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落叶的神情。
我觉得城市是一面骄横、自大、善于夸张与歪曲的镜子,在它面前,我们已得不到客观的反映,城市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反映被扭曲了的我们。
与上海比较,与香港比较,与纽约比较。
如果再掠去我们这里几座有限的楼房,我们这里多么像一个庞大的废墟。
据说联合国的人到这里来过,结论说,你们这里的自然境况不适合人类生存。
但这里毕竟生活着近二百万血肉之躯啊,他们毕竟在有了那样的结论之后依然日复一日,勤勤恳恳地生活着啊。
不久前我到过红羊乡一个叫杨庄的村子,这个村子原本就偏僻得不能再偏僻了,绝境得也不能再绝境了,但我的一个亲戚不知什么缘故竟率领几个儿子又搬回原来的老村子去了。
那是一个尚未通电而且没有通电指望的村子;那是一个像枯石头一样没有水源的村子;那个村子,也只有他们爷父三户人。
我跟着他的儿子到他们家里去。我们不是在坡上走着就是在沟里走着,或者就在细细的崖畔上走着。正午时分,野风突兀地显出形象,在空无一物的地上狂躁地旋一旋,又莫名地消失了;无穷无尽的大山耐心地等着你自己被风化掉,在这样的地方走着,禁不住就生出一种恐惧感与虚幻感,觉得如今是返也返不回去了,走也走不到了。一切繁华之地一瞬间都变得那样渺茫,几乎渺茫得不可想象。
这里,连一辆架子车也不能走。问吃水怎么解决,说是到远处去买,一囊水20块。在城里不足两块吧。他们原本是近乎赤贫的人,他们却要用高出城里人10倍的价钱买水吃。
我问亲戚的儿子,白天一个人在这里走,怕么。我们年纪相仿,他却显得比我苍老得多,自然要憨厚地笑一笑,轻描淡写地说:“半晚夕也走的。”
我承认我受了很深的震动。
我想,这些人一定有着一种奇异的心灵。
但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如此的忠厚勤勉之土,为什么总是在一种外人不可思议的绝境里咬着牙生存。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种种缘故而降低人的品位。
请看我们把那个亡人抬举得多么高啊,请看那些被有限的水洗得多么干净的脸,请看那一个个顶着净雪的头颅,请听一听那使高天为之洁净肃穆的乐章。
我们从来都不敢低估人和人的可能性,我们从来都知道人的尊贵,即使赤贫若洗,也依然不改其尊贵,我们从来都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块可能被掩盖,可能会丧失的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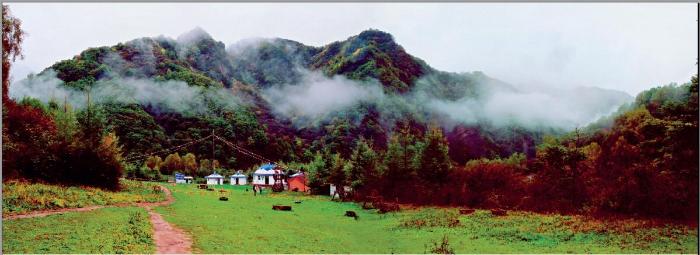
我们也没有因种种缘故而麻木于对欢乐的感知。我们是所求不多的,我们基本会给她穿上一身鲜鲜的红衣裳,使她像一团夜晚的火焰,我们会让她羞怯地坐于小青驴上,轻轻走过苜蓿花开的路边,我们会邀请万万千千的蜜蜂与蝴蝶与我们共行。
包括那些生活在最繁华最优秀的城市里的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述说起城市的种种不是了。然而西海固人,他们依旧深深地眷恋着这块古老的苦土,他们自己不愿说这里的什么,他们也不愿别人议论这里的什么。
是否有一种什么启示?
是否有一种另外意义上的可能性?
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
我们有那么多的弟兄神情庄重地将笔拿起。我们想把我们的笔尖探索到我们的身体几乎无望到达的地方。
西海固是否是一块文学艺术的厚土。
我想是的。
其实不是我想,很多有识之士都这样说过。
其实也无须说。
我有时龟缩一域,耽于冥想,我像反刍一样,让一些面孔缓缓掠过我眼前,让一些珍存的情景缓缓掠过我眼前。
老实说我觉得很幸福。
我觉得很富足。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在精神上是充盈的,不欠缺的。有时也狂妄地觉得我们或我们的后辈会在精神领域长出很大的翅膀。
有好几天,我在我们那个县城的街上走,街上空荡荡的,强烈异常的阳光使我们那个街道如一卷翻开晒着的老书。正午,不多的几个人在亮亮的阳光里活动着,一瞬间某种强烈的东西将你袭击着了。我对一个朋友说,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潦倒一生、伟大千古的梵高和他的阿尔来。
看过伏兆娥的剪纸,听过马生林的花儿,我都受到过强烈的震动。
我可以不听毛阿敏,可以不听韦唯,我可以不听很多。
但不听马生林,在我就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然而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都困守一域,走不出去?
这是值得我们再三思之的。
幸好在文学领域,当代一位极优秀的作家已为西海固的可能性做了有力的证实,因为他们的原因,有人在复旦等一些知名大学像讲解一片圣土那样讲解着我们的西海固。
但着实说,我们的笔还差得很远。
我们目前只是知道了这种可能性,知道与将这种可能性实现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得握牢我们的笔,我们得更加地多一份谨慎与不舍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