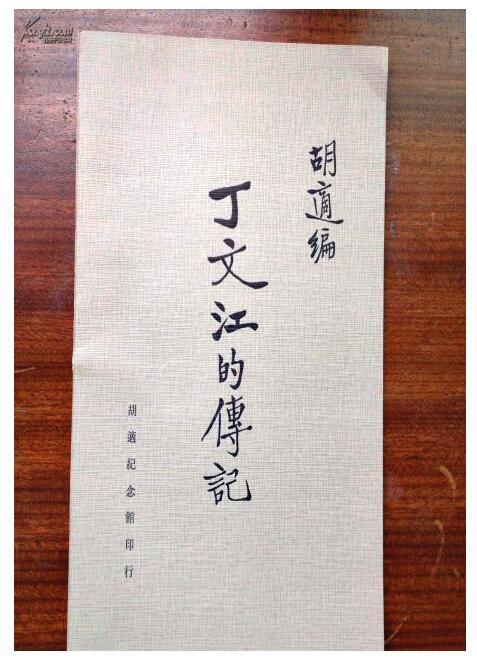
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他不仅是一位思维敏捷、博学多才、勤于实践、治学严谨和开拓创新的人物,而且还是一位乐观开朗、热情友善、勇敢果断、坚忍不拔和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丁文江短暂的一生对国家、社会、科学以及朋友、同事、老师、学生和家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处处散发着炽热的人格魅力。我们被丁先生的高尚品德、独特思想和非凡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将会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弘扬这种人格魅力,我们相信地质界、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会受益良多,同时,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在对搜集到的有关丁先生的文献资料整理后,总结出丁文江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敏于求知 学贯中西文化
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大家族。4岁入家塾读书,学四书五经;10岁时已能文,作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丁文江幼时在家乡接受的严格私塾教育,为他一生的传统文化和文字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5岁时,他开始了留学生涯,历时9年;先日本,后欧洲。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丁文江广泛阅读科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书籍,不仅获取了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形成了一个科学家的思维。他于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多年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使他最终成了“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正因为这样的学习背景,造就了他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他在地质学、天文学、动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人种学、地理学、地图学、哲学以及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均造诣很深,驰名中外。他能阅读俄、法、德、日、英等文字的书籍,能说英、法、德三国语言,英文尤为流利。难怪黄汲清先生曾评价说:“丁文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尊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这些学习背景,使丁先生具备了中西文化贯通的多学科知识,为他日后对国家、社会以及科学的思考和贡献奠定了基础。
勤于实践 考察地质现象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质工作尤其要重视野外调查工作。丁先生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不避严寒酷暑,身体力行地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教育、培养了一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地质人才,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外国地质学家发起,其中著名的有美国人庞培勒和德国人李希霍芬,等等。他们在中国建立地质调查机构之前对中国地质的调查和研究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李希霍芬这样评价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历来是迅速行动的一种障碍,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本国体面的成见。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单从事的。”丁文江对此则不以为然,但他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和我国自己培养地质人员的成绩证明了中国学人是有行动力的。实践后他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获得双学位就取道越南回国,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考察,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
丁文江对野外实践工作的重视,也体现在他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中。他说“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他不仅仔细阅读了《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新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敬佩。
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他这种重视野外调查的工作方法和不怕苦的精神,为后起的地质工作者,树立了良好榜样,对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善于思考 悟出科学思想
丁文江的留学生活和实践经历,养成了其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他通过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以及他在实践过程中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最终形成了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胸怀,形成了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
丁文江崇尚科学的高尚信仰,在行动中“以科学知识为向导”。1934年,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其中从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151号、丁文江《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自然》周刊、丁文江《中国现代科学》、丁文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从这些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摒弃旧的“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发扬光大。丁文江是一位有抱负的思想者,始终保持科学家本色。
丁文江所处的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了勤奋好学、勤于实践外,还在于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致他能够独立思考,悟出科学的思想和真谛。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来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勇于创新 解决实际问题
丁文江勤奋好学,重视野外调查,搜集事实材料,善于总结思考,所以他能够在学术勇于不断创新。他能对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矿业、交通以及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实与他能运用科学方法,不断获得新的事实材料分不开。丁文江先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多学科工作的推动者。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也是中国古植物学的奠基人。后来,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他对早期古植物学的艰苦创业和贡献分不开的。与古植物学一样,当时的古脊椎动物学在我国也属空白。为创建该学科,丁先生还派杨钟健去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总之,丁文江先生以“立足自己,争取外援”和运用“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做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中国古植物学乃至古生物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人才迅速成长,研究成果连续发表,促使学科迅速发展,并已广为世界所知。至此,中国古植物学已初步形成,它作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出现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并加入了世界科学之林。而丁文江先生及其功绩则是该学科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
此外,丁文江对史学的首要贡献是用其他学科研究历史,最早的贡献是用优生学的知识研究中国的谱牒。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贡献是用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二十二史上的人物籍贯的统计,研究了“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正因为有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造就了丁文江先生的许多第一,这种创新精神是我们今天做科研工作需要发扬的。
敢于担当 服务国家民众
丁文江是一位用自己的行动为国家和民众服务的爱国者。他对我国地质学的创建是科学救国的一件实事,他以自己的知识为国家服务,不存在利己之心。葛利普说:“丁博士以超人之才识与能力为其祖国服务,从来不为私图”。
丁先生的服务于人民大众,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动准则的理念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他多次呼吁少数人应当并能够担当国计民生的大责任,而且终生身体力行,就是这个理念的表现。因此他论人治事每常以实践成效为准。
1934年发表的《我的信仰》一文中,丁文江先生把自己的信仰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要做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为,就是做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第二,要以科学知识作为行为的向导。在这里他回答了人生观的两个基本问题:要为社会的最大多数人服务,而服务的方法则是要倚赖于科学。
丁文江在《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演讲中,他说:“……今天的青年……应该要十二分的努力,彻底地了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今天,我们的青年更应该如此。
甘于奉献 不计个人得失
丁文江心怀大志,爱我中华,在人生的征途上奋发进取,甘于奉献,牺牲自身利益,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1910年,留学时,丁文江和李祖鸿在张轶欧的帮助下,有了补全官费的希望。因丁文江马上要毕业回国,就把官费让给了李祖鸿。而李祖鸿不但补了夏间的官费,还从这年的1月起一次性补给了100多镑。
1934年,听说云南教育厅请孟宪民等去云南做调查,丁文江连夜将自己从前在云南调查所得之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交给孟宪民等参考。可见,他对同事、对公益事业,是何等的无私。
丁先生竭尽全力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考古学家李济说:丁文江“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到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丁文江牺牲自我造福青年的奉献精神,要学习他克服困难创办教学机构的奋斗精神,还要学习、借鉴他按教育规律办事所采取的许多举措。例如:制定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方案;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在主要学科方向上聘请高水平教师;开展广泛国际合作;树立严谨的学风,等等。
严于律己 坚持廉洁奉公
廉洁奉公是丁文江的一贯理念。他作风正派,从不以权谋私,无论在地质调查所,还是淞沪商埠总办任上,亲友上门请托,他都一概拒绝。他不为家人申请留学公费而由自己负担。他两袖清风,不置私产,有兼职而又受兼薪,在辞世前还留遗嘱将自己的藏书和一部分财物捐给中国地质学会。
傅斯年说:“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干薪。”他不但不占公家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他还要牺牲私人的利益,以成全公家或他人的利益。丁文江离开地质调查所的原因,主要是他家里的经济负担太重,每年多至三千元,靠地质调查所的薪俸不敷应用。
1934年,丁文江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那时,国力不强,经费有限。丁先生一上任,就宣布裁撤总干事属下的庶务处,将国际出版品交换处移归中央图书馆办理,只保留原有的文书、会计两处。丁文江所以要进行机构精简,是为了节省出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研究事业。此举可体现丁文江的工作理念:一切以研究为中心。
丁文江这种严于律己,坚持廉洁奉公的精神正是当前社会所宣扬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乐于助人 关心亲朋好友
丁文江乐于助人,对家人、亲戚、同事、朋友和学生都是无微不至地关心,这种责任感是极为真挚、感人至深的。
对待家人:学成归国后,先后将他的四个弟弟并年长的一兄、一姊和一个弟弟的子侄辈接出来念书,接受教育,有望成大器者则送往国外留学;而受丁文江栽培的子弟,均各自有成。
对待夫人:丁文江与夫人史久元结婚后,感情甚笃,这在朋友间传为佳话,傅斯年就曾说:论到在君之对家庭,真是一位理学大儒。他对于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极其恩爱的。他们两个人的习惯与思想并不全在一个世界里,然而他之护持她虽至新至少年的恩爱夫妻也不过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值得敬佩的女士,处家,待朋友,都是和蔼可亲,很诚信,很周到的,并且对两方的家庭都是绝对牺牲自己的。她不断地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仅做她的保护人,并且做她的看护生。他真是一个模范的丈夫,无论在新旧社会中,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对待老师:龙先生的知遇之恩,丁文江终生感念。他不止一次说过: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那样早出洋留学。1911年,他自英国学成返乡,路经湖南,专门到长沙拜谒恩师。1935年12月2日,丁文江再次来到湖南,下车伊始,即表示:到湖南一定要看两个人,一是胡子靖先生,第二个就是师母龙研仙夫人。12月5日,也就是他煤气中毒前三天,徒步登上了海拔1 000多米的衡山,拜谒龙研仙先生纪念亭。
对待友人:丁文江一生,交友极广,自政要官员、军阀首领,到学界名流、工商巨子、海外一流学者,都有他深交过的朋友。凡是和丁文江有过深交的人,无不感于他对朋友的诚厚,无不对他的交友之道交口称赞。在他逝世后,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一文中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恶事,他都操心者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正因为他对朋友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甚至超越朋友界限关心,所以,朋友总喜欢称他作“丁大哥”。
对待学生:丁文江很重视青年地质人才的培育,惜才、爱才,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关怀。他对赵亚曾的青睐,对谢家荣、朱庭祜、王竹泉、杨钟健、李春昱、黄汲青的栽培,处处显示着他的提携后进的精神。因此黄汲清说“丁先生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提拔和使用人才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成绩很大影响深远。他是20世纪的伯乐”。
丁文江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对待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待友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对待晚进后学则亲切教导、百般关怀、热情扶掖,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也是我们要铭记和学习的。丁文江卓越的领导才能、精心的策划和具体实践能力,不仅是对中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他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


